用一种有效的安慰疗法来救治病人
便扪心自问,他们也很难承认,他们在行医过程中竟然会使用安慰疗法来增进患者的健康。假如一个医生,不管多么不情愿,但他可以使用一种有效的安慰疗法来救治病人,那么,他应该积极热心地去开这个处方吗?说到底,医生对一种治疗方案是否热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疗效。
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关美国的医疗保健事业。美国的医疗保健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们感觉高价药品(50美分的阿司匹林)比低价药品(1美分的阿司匹林)更有效这一现实呢?我们是该放任人们的非理性,继续提高医疗保健的成本呢,还是坚持要求人们使用市场上最便宜的普通药物及医疗手段,而不采用那些疗效更好、价钱也更贵的新药呢?我们该如何建构成本与共同负担的医疗机制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如何让需要的群体能买到廉价药品而不降低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医疗水平?这些都是建构医疗保健制度最关键、最复杂的问题。
安慰疗法和安慰剂也令市场营销人员左右为难。职业道德要求他们创造可预期价值,但如果过度宣传某个产品的客观价值,根据夸大的程度,就可能成了歪曲事实,甚至成了散布谣言。我们看到,对医药、软饮料、大众化妆品和汽车来说,预期价值可能成为真正价值如果人们从某一产品中获得了比较大的满意度,是否就是营销人员炒作的结果呢?我们对安慰疗法想得越仔细,对信念与现实之间的模糊界限考虑得越多,这些问题就越难回答。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认为,对我们的信念和各种医疗方法的疗效所实施的实验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我很清楚上述实验,特别是关于医学上安慰疗法的实验,引发了很多伦理问题。的确,我在这章开头举出的胸廓动脉结扎手术问题就引起了伦理方面的争议:很多人强烈呼吁,反对给病人实施假手术。
为了弄清楚某一疗法是否应该继续使用,就把它暂停下来,这样很可能牺牲眼下一些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想到这里就让人很难接受。例如虽然一个患癌症的孩子正在接受的是安慰疗法,为的是几年以后患同样病症的其他人可能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但这仍令人难以接受。
同时,如果因此而停止安慰疗法的实验,同样令人难以接受。这种疗法可能会让成千上万的人接受无作用(有风险)的手术。在美国,各个步骤都经过科学测试的外科手术很少。因此,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很多手术是否真能治愈疾病,或者像从前的一些手术一样,是因为安慰疗效才取得效果。由此,我们会经常想,是否应该先更仔细地研究某些疗法和手术,在真正弄清楚它们之前不要行动。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关于一种治疗方法,我觉得我是受了虚假宣传的引诱。但实际上,我不过是经历了一次痛苦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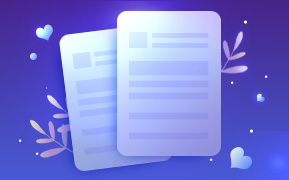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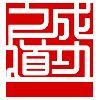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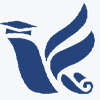
评论0
“无需登录,可直接评论...”